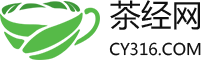【www.cy316.com - 红茶铁观音】
初识铁观音
早年喝茶,喜欢花红叶子泡的茶。花红是一种落叶小乔木,叶子卵形或椭圆形,花粉红色,果实球形,黄绿色带微红。花红叶子泡茶有树木的原香,略甜不苦涩,味域颇宽。夏天工厂车间和学校的大瑭瓷桶里都是这样的茶,系牛饮族豪饮之经典茶水,我以为粗茶淡饭里面的粗茶,便就是花红茶罢。
成年以后,知道花红叶子乃茶之赝品,就着力隐瞒喝花红茶的历史,且言必称龙井云雾,还有银针碧螺春,就如当年写诗言必称北岛舒婷,仿佛这样就真正地懂茶了。显然,拿着名茶说事的人,并非是日常皆饮名茶,如今谁人称其一年365天皆饮名茶,我也怀疑。所以,我决定不隐瞒自己喝花红茶的历史。
我印象中喝到的地道名茶应该是铁观音。有一个秋天,天高气爽,日丽云白,有排成人字形的大雁从天空向南飞去,大箕山上的枫叶红了,水南湾的河水清清地向东流去,田畈间收割的人们晃动紫铜色的膀子,他们割下金黄色的晚稻谷,然后握着弥漫青甜气息的禾秆在围着篾席的挞谷桶前嘭嘭嘭地挞谷子,山岚依地漫起,给远村轻笼一团青色。秋天了,它是一个斑斓的季节。我的同事黄正华弄回来一罐茶叶,早早通报于我和另外几个文友,说是有名茶铁观音,下班去他家喝茶。
下班,这一帮感觉里面充满情调的家伙就披着白衬衣往黄正华家散漫地走去,黄正华家在街旁,是一个废弃的小矿山的街,平房,那地方叫叶花香。印象中各家厨房的平顶上,砌有花坛,种植了辣椒和小白菜。在门口摆好椅子,说是就在此喝茶。很有些张扬的样子。等着黄正华煮水泡茶。水是拎的井水,煮沸了,茶具是一套当地生产的“宜兴紫砂壶”,人各发一紫砂杯,看着黄正华给我们涮杯、洗茶、闻香,然后就结结实实地将茶泡上。果然,铁观音是有一缕幽兰芬芳,十分好闻。正待要喝时,黄正华又抓出一把新牙刷,说,刷牙刷牙,晓不晓得这是喝名茶?于是,我们一干人等为了名茶,就排在街旁的旱水沟前,在斜阳金辉里愉快地刷牙。其时心里觉得很神圣,或者很上等,很高级,从此我们就是懂得喝茶的茶客了,我们马上就要喝名茶铁观音,这一街来来往往的人,他们懂么?十大名茶铁观音呢,是一个方形的铁皮盒子装的。
刷了牙,就开始喝茶。我们皆执起杯,眼睛则一齐瞟着黄正华,黄正华自然要带头,大厚嘴唇片子抿着紫砂杯有力而艰难地吸上一丝茶水入口,发出吱的一声,我们皆仿照而行之,便有一阵吱吱声,如是群鼠出洞,声不绝耳。人也就感觉,兰花香绵的安溪铁观音,自口而入,至咽喉而回旋鼻腔,如香云袭卷,游丝悠颤,便将感觉的通道轰然炸开,是一枚兰花炸弹。铁观音汤色清浅黄亮,味甘润又略有微涩,其后是淡淡的甜尾,像苹果园的夕阳,夕辉渐远,浮香而别,然其香仍绕舌三匝而徐徐不绝。这回是共喝了六泡,居然有些醉茶,从没有遇到过。出门了,铁观音余香袅袅,想来确实是好茶呢。
严格算起来,黄正华应该是我喝茶的师傅,包括我的那帮同事。但是因为他曾经在喝茶之前指挥我们集体刷牙,就又都不愿承认他是师傅。喝罢铁观音,黄正华说他要弄一些正宗的西湖龙井,再喝,这又把我们镇住了。以后,就把喝茶当一件事情了,而不惟解渴。茶香一去三千里,旧饮新啜两分明。
Cy316.com延伸阅读
到禅门吃茶去
不管你是佛教信众还是红尘中凡人,赵州的柏林禅寺总在无言地召唤着你。且不说寺内飞檐翘角装得下万尊佛像的万佛楼,不说古柏参天绿色掩映中的赵州和尚舍利塔,不说青灯古卷、晨钟暮鼓、梵音缭绕。单是一杯飘着淡淡清香的赵州茶氤氲着的几多禅意、几多空灵,就足以叫人心驰神往了。
柏林寺就座落在我居住的小城里,我极是熟悉。寺院距我家不过两华里,距我姨哥家也就一墙之隔。儿时的我,没有什么现代儿童所享有的游船、过山车、蹦蹦床等等之类的游艺设施。于是,古赵州芳草萋萋的城墙、彩虹般的赵州桥以及柏林寺,就成了小伙伴们最常去的地方,那时,柏林寺远不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样子,只有几株苍老的古柏,几通东倒西歪的石碑,一座显得荒凉的砖塔和大片废墟。我们在这里捉迷藏,攀古塔,时常忘却吃饭,直到家长来唤才肯回家。
后来一位叫做净慧的大和尚重振宗风,将赵州柏林寺建成中国北方最大的寺院之一,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柏林禅寺。知道赵州茶,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且常常疑惑,赵州本不产茶,赵州茶却何以名扬天下?
一个偶然的机会,翻阅《光绪赵州志》,见有如下记载:
“活泼泉,在柏林寺后,最寒冽,宜于烹茶。往来嘉宾过柏林寺者,及观画水,复饮香茶。盖悠然物外矣。”《光绪赵州志》还记载了有关赵州茶的诗句。如:“忽忆禅房旧念生,由来茶味有余情”。“吃茶参妙理,水底一灯明”。“冷冷林空古壁水,如如禅语赵州茶”。
接着,在离我们生活年代更近一些的资料上得知: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在永安院居住时,从我国南方引种茶种,在寺内开一茶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始赵州茶成为过往僧俗必饮之香茗。再后来,荣西携茶种回国,赵州茶便在日本得以流行。
在我看来,赵州的确是不产茶的。至于赵州茶如此出名,不应该从当地产不产茶来考虑、不应该从历史和古籍里去寻觅茶踪,这样的话,恰恰失去了赵州茶应有的馨香和韵味。如果想了解赵州茶的故事,想体味“禅茶一味”的妙境,那只有当下到赵州吃茶去。赵朴初先生讲得好:“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那么,这“吃茶去”典故出自何处究竟何意?
那一日,陪省报赵先生等邯郸朋友一行,到柏林禅寺参观,拜会了明海大和尚,大和尚一袭僧衣,骨骼清奇,清癯的面庞透着祥和。当侍者将一杯香茗捧至桌前,明海大和尚笑微微地向我们讲述了禅门关于“吃茶去”的机锋公案:“1300年前,唐代的从谂禅师学得南宗禅的奇峭,80岁时常住赵州观音院,人称‘赵州和尚’。一天,学人来拜见,赵州和尚问:‘你来过这里吗?’‘来过’。‘吃茶去’。又有学人来拜见,赵州和尚问:‘来过吗’?学人答:‘没来过’。‘吃茶去’。在一旁的院主不解,上前问:‘怎么来过这里叫他吃茶去,没来过这里也叫他吃茶去?’赵州和尚答:‘吃茶去’。”
故事讲完就有友人问:“‘吃茶去’讲了一个什么道理,有什么含义”。明海却笑而不答。我以为吃茶去,实在就是一个禅故事,笑而不答就是回答。
母亲敬佛也爱茶,每每坐到母亲面前,她总是把自己最珍爱的好茶与我分享,这茶是她多年前的老朋友和现在的新朋友相赠。茶好得可以,也是十分有名的茶,许多种我都叫不上名字。但当我看到日渐变老的母亲,用不再光滑的手,为儿子斟上一杯饱含亲情的茶水时,我的泪在流,但却不敢让她看到,只好流在心中,生怕她难过。这时候我就觉得禅就在母亲这杯茶汤里了。母亲为我斟茶,她是在教育我如何回报生我养我的母亲。我也在想,什么时候才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来报答最最亲爱的母亲,来为她泡一杯天下最好的茶。母亲泡茶的时候,是慈祥的,但从没有要求儿子为她添添水。当我为母亲提壶续水的时候,她指着玻璃杯中沉沉浮浮的茶叶说,这就是人生。莫不是母亲参透了“功名利禄来来往往,炎凉荣辱沉沉浮浮”。莫不是在教导我,求一分淡泊,得一分宁静,保持一颗平常心?
母亲与明海大师结缘已久。当她还是县城里一个小小图书馆长的时候,就常有一个谦逊的小和尚,到馆里来借车,那车本是宋庆龄基金会所赠。小和尚借车就是为重振柏林寺做些事情,屡次借车之后,那小和尚感恩图报,将他在一所名牌大学时所读的书,送一部分给图书馆。那和尚说,如果你儿子喜欢就选几本吧。我尊重这个有学问又聪明的小和尚,所以就高兴地拿了一些保存起来,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小和尚就是现在的明海。
光阴如梭,多少年过去了,因了那时的因缘。母亲与明海成了忘年交。从此,她不再提念过去一些对不起自己、甚至令她伤心的人,却常常把明海大和尚像亲人一样挂在嘴边。这倒是我们做儿女的所欣慰的,至少,她忘记了仇恨,这对老人的健康大有裨益。
母亲就是儿子心中的佛,是值得儿子品味一生的茶,是一生都参不透的禅,是一辈子也敬不完的佛。
禅,就在母亲泡的茶水里,就在每个人玻璃一样晶亮的心里。吃茶去。
想不老,吃茶去!
青春如花,然而花期短暂。
自由基的破坏活动是人体衰老的罪魁祸首。衰老固然不可避免,但是总可以让衰老的脚步放慢些,再慢些。
绝大部分女性求助于化妆品。但遗憾的是,衰老的因子,更多产自身体内部。依靠化妆品可以清除一部分色斑、让肌肤紧绷、隔离紫外线、掩盖黑色的毛孔,但是如果无法将身体内部的自由基及时清除,衰老还是无法抵挡。
幸亏有茶。现代研究表明,茶是天然植物中,清除自由基能力最强的一种。
茶多酚对各种氧化酶均有抑制作用,可以高效清除自由基,是见效最快的抗氧化途径,同时能抑制自由基的产生并激活人体的抗氧化酶体系;研究表明,茶多酚的抗氧性明显优于维生素E,抗衰老效果要比维生素E强18倍,且与维生素C、E有增效效应。
我们可以简单地用茶叶浸泡洗脸或者调和蜂蜜做成面膜,去获得清除面部油腻、收敛毛孔、灭菌、抵抗紫外线辐射对皮肤的损伤等功效。
我们更可以每天喝几碗茶,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人体的自由基有90%源自肠道的非正常发酵,所以,一碗清新抹茶,几乎可以把这些自由基统统清除。多么简单啊!
更重要的是,茶儿茶素通过抑制肠道中的消化酶来减少肠道组织对碳水化合物、脂类的吸收起到抗肥胖的作用;茶多酚可通过抑制体内脂肪沉积和促进多余脂肪的分解实现对抗肥胖。科学研究证明,肥胖不利于清除自由基,所以对于女人抗衰老、清除自由基来说,吃茶本身就有着一用多途的美好。
所以,我们理解有很多女性为什么即使60岁了,皮肤依旧同小姑娘一样,因为除了饮食、化妆品之外,她们懂得“吃茶”。
懂得吃茶,不仅仅能够很好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懂得茶道,更可以让你的心情随时平和起来,姿态优雅起来。人的衰老,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岁月如梭,有茶不老。
吃茶去 宜兴红茶
这年头是事都讲究知名度,有没有名气很重要。现成例子是紫砂壶,一提到,立刻想起它的出产地。我惦记的是宜兴红茶,怎么都忘不了第一次喝时的惊喜。是个老茶客推荐的,喝了以后,满嘴生香,久久不能忘怀。我对喝什么茶,一向没什么讲究,只要是好茶,都爱喝,都能喝。喝好茶就像上馆子,图的是嘴上快活,犯不着死钉上一家饭店不放。一年四季气候不同,环境各异,用心去品,是好茶都能喝出味道来。
知道宜兴出红茶的人不多,知道宜兴红茶是好茶的人更不多。说到喝茶,时髦话题是这茶多少钱一斤,昂贵成了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最新,最嫩,更要包装好看。一个朋友告诉我,如今的茶农都知道往茶树上喷药,这药作用神奇,能让茶树立刻长出新芽,结果吃新茶犹如喝春药,得了病,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往高处走,话往大处说,宜兴红茶价格便宜,便宜了反而无人问津。
听说最初喝红茶的都是些窑工。所谓窑工,就是烧紫砂壶的人,由此可见红茶本来已有民间基础。老茶客让我好好琢磨琢磨,仔细想想紫砂壶与红茶的关系。绿叶衬红花,骏马配好鞍,凡事都要考虑一个合适。紫砂壶泡龙井碧螺春,那是暴殄天物,是老牛吃嫩草,是粗壮的黑大汉糟蹋未成年小女孩。紫砂壶天生是为红茶准备的,要用紫砂壶,就得喝红茶。要想品味好红茶,必须是紫砂壶。
这就好比生了周瑜,就应该再有个诸葛亮,否则拔剑四顾无对手,只能孤独求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紫砂壶非常风光。台湾商人一窝蜂拥向宜兴,一时间,好多人暴富,有把好手艺的趁机赚钱,闷声大发财。紫砂壶和红茶,按说应该共生共灭,共同繁荣和发展,事实却是,紫砂壶成了白天鹅,红茶仍然还是丑小鸭。紫砂壶孤军深入,名声越来越响,价格越来越高。高不一定是好事,爬得高,摔得也重。谁都知道,现在的紫砂壶市场已经惨不忍睹。
一把紫砂壶可以卖出天价,卖了也就卖了。人们大约不会想到忽视宜兴红茶的恶果,唇亡而齿寒。紫砂壶在台湾能够风光,显然与乌龙茶的冲泡方法有关。我不明白宜兴人为什么不隆重推出自己的红茶。江南人爱喝绿茶,这不错,爱喝并不意味着只喝。茶有许多种喝法,非明前雨前不喝,一味追求尝鲜是时尚,用紫砂壶泡红茶,同样可以赏心悦目。价廉而物美,又有古风,何乐不为。
忍不住要为宜兴红茶吆喝一声。“养在深闺人未识”,不是好事。酒香也怕巷子深,西施不是进了吴宫才成为美女,要是不被夫差宠幸,她到死也只能是个默默无闻的浣纱女。
品茶知味 碧螺春汛“吃茶去”
碧螺春汛
山坞里静煞,就连喜欢吵吵笑笑、多嘴多舌的鸟们,也还春眠正酣。只有兰娣和另外几个迎接茶汛起得绝早的小姑娘,在山坞里挖笋、采蕈。春分时节,正是梅蕈、松蕈、黄栀蕈开始旺发的季节。
兰娣一不挖笋二不采蕈,她在替公社的香精厂采蔷薇。她翘起灵巧的指尖,避开桠枝上刺手的短针,飞快地把一朵朵白花拗进桑篮里。
淡蓝色的晓雾,从草丛和茶树墩下升起来了。枸橼花的清香、梅和松花的清香,混和在晨雾当中,整个山坞都是又温暖又清凉的香气;就连蓝雾,也像是酿制香精时蒸发出来的雾气。
忽然,缥缈峰下一声鸡鸣,把湖和山都喊醒了。太阳惊醒后,还来不及跳出湖面,就先把白的、桔黄的、玫瑰红的各种耀眼的光彩,飞快辐射到高空的云层上。一霎间,湖山?上空,陡然铺展了万道霞光。耀花眼的云雀,从香樟树上飞起,像陀螺样打转转,往朝霞万里的高空飞旋。在沙滩边和岩石下宿夜的鸳鸯、野鸭,也冲开朝霞,成群成阵的向湖心深水处飞去。
村子里也热闹起来了,羊子的唤草声,孩子刚醒转来口齿不清的歌声、笑语声,火刀石上的磨擦声,水桶的磕碰声……
钟声送走了宁静的黎明,迎来了一个新的劳动日,迎来了碧螺春汛的头一个早晨。
茶汛开始的辰光,一簇簇茶树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桠梢上一枪一旗刚刚展开,叶如芽,芽如针。可是只要一场细雨,一日好太阳,嫩茶尖便见风飞长。
茶汛到了,一年中头一个忙季到了,头一个收获季节到了,个个人都开开心心的,真像是过节一样。就连小学生也欢欢喜喜地读半天书放半天茶假,背个桑篮去采茶。
采茶采得清爽、采得快,全大队没啥人敢跟兰娣比赛。往年,兰娣采茶的辰光,在她的茶树墩周围,时常有几个小姊妹,似有心若无意地跟她在一道做活。阿娟总是拿妒羡的眼神,斜眼偷瞟兰娣灵巧的手指;云英却衷心敬佩的、从正面紧盯住兰娣的动作。今年,开采的头一天清早,一下就有十几个唧唧喳喳的友伴,围拢在兰娣茶树墩的四周。十几个小姑娘,都急忙想学会兰娣双手采茶?本领。在我们这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老茶山上,兰娣,是头一个用双手采茶的人。
别处名茶区的茶树,都是几百亩上千亩连片种植。茶树墩横成线竖成行;树冠像公园里新修剪过的冬青,齐齐整整。但我们这个碧螺春故乡的茶树,并无大面积连片茶园,它散栽在橙、橘、枇杷、杨梅林下,成了果林间的篱障。茶树高高低低,桠枝十分杂乱,但兰娣的双手,却能同时在参差不齐的桠梢嫩芽尖上,飞快地跳动,十分准确的掐下一旗一枪。大家形容她灵巧的双手“就搭鸡啄米一样”。虽然她的手那么灵活,又那么忙碌,但兰娣的心境神态,仍旧跟平常一样,左?流盼,不慌不忙,悠悠闲闲的和友伴们讲讲笑笑。
围在兰娣身边的小姊妹,都拿眼光紧紧地盯牢她的双手;同时,也在自己的心里,替兰娣的技巧做注解、做说明。阿娟,甚至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兰娣双手采的窍门,可是自己一伸出手来,马上就眼忙手乱了,不是顾上左手忘了右手,就是眼睛和手搭配不起来。她苦笑笑说:“看人家吃豆腐牙齿快,看看兰娣采,容易煞;看看,看看,眼睛一眨,鸡婆变鸭。”
云英干脆问兰娣,她是怎么样才会采得这么快的。兰娣笑笑说:“我也讲不清爽。喏,就是这样采——”兰娣是个心灵手快但是嘴笨的姑娘,?家都晓得她确实是会做不会讲啊。
后来,阿娟和别的小姊妹们,虽然学会了兰娣的双手采,但产量仍旧落在兰娣后边。每晚歇工的辰光,队长和社员们一碰见记工员,头一句话常常是问:“兰娣今朝采仔几斤?”兰娣采几斤,成了黄昏头歇工时全队顶顶关心的事情。
队里一向有这样一个习惯:每天夜饭后,除了几个困早觉困惯了的老老头之外,全队的人,差不多都聚在俱乐部的厅堂里,有时开会,就是不开会,也欢喜三五个要好的朋友,围坐到一张台子边;泡一壶茶,摆几只共盅,抽抽旱烟,云天雾地的谈谈闲话。妇女们常常是就着桅灯纳鞋底、结绒线,缝补衣裳。孩子们趴在台子上做功课,有时也追逐打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