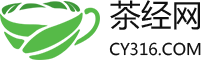墨茶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文人茶趣|司马光与苏轼间的“墨茶之辩””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文人茶趣|司马光与苏轼间的“墨茶之辩””相关知识!
在中华传统文化里,经常把书香、茶香、墨香并提。书香悠悠,茶香逸逸,墨香淡淡,三香萦室,都是人生的美滋味、美境界。这秋日的夜晚,明月在窗,虫声在耳,研墨试笔,品茗夜读,书、茶、墨香香生色,足以醉满心池。
为人不知的是,宋朝文人大都为品茗行家、斗茶专家。明人屠隆在其所著《考盘余事》中就记载着一段苏轼和司马光之间关于茶与墨的辩论,是当时的一段佳话。
相传,司马光好茗饮。一日,邀好友斗茶品茗,大家带上各自收藏的上好茶叶、精美茶具、甘泉良水赴约。先看茶样,再嗅茶香,后评茶味。苏东坡和司马光所带的茶成色均好,但因苏东坡自携隔年雪水泡茶,水质好,茶味纯,于是占了上风。司马光内心略有不服,当时茶汤尚白,他乘机出题玩笑苏轼: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君何以同爱二物?苏东坡不慌不忙,高睨而答:二物之质诚然矣,然亦有同者。司马光不解,问其原因,苏东坡从容而道: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以为然否?话毕,众人皆服。
这便是广传于文坛和茶界的墨茶之辩。其虽为文人逸事,但却是文人们最精致的心灵的证明。如林语堂先生所言,苏东坡像一阵清风过了一生,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东坡先生一生踏遍天下,虽屡遭贬谪,却随遇而安,得以尝尽溪茶与山茗,更兼得茶中三昧,最终悟得茶道至境。古人云:深心追往。我们惟有深心,才能追往。墨茶之辩中司马光、苏东坡一问一答中充溢着人生哲理,也意蕴着智慧的启迪与升华。
茶是一种人生。按中国汉字的书写方式,茶上为草,下为木,中为人,即人以草木为邻,与万物共生。人们面对自然的态度,更应是追寻内心所向的一种尊重和执着。师法自然,以敬畏之心唤醒茶中的极致内蕴、至洁灵性,做世上最纯粹的茶才是行中大道。
cy316.com编辑推荐
文人与茶
茶是中国最古老最普通的饮品。或说茶是苦菜(许慎《说文解字》),或说茶为南方之嘉木(陆羽《茶经》),那只是说了茶的植物性一面;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论茶也。(许次纾《茶疏》)茶与水结合才能尽显茶的本色。茶,是茶叶与水的共生物。
文人在文房四宝的拥戴中枯坐,一经吮茶,立刻以狂喜之心拥它入怀,轻啜慢品。茶是自然的、圣洁的,茶是优雅的、纯粹的,茶是温情的、清芬的,它使整个书房溢满氤氲。文人之于茶,犹茶之于水。在清冽的汤泉中叶芽舒展,文人的心境亦平展夷畅,此时将天地之甘露入肠,清心涤性,臻至物我两忘之境。
文人咏茶,总是在一片芳馨中孕育出无数佳作。尤其茶助诗思、诗兴遄飞,令人击节赞叹。
最有趣的是,文人咏茶往往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不经意间成为一部茶史。大哉天宇内,植物知几族?灵品独标奇,迥超凡草木。苏轼《寄周安孺茶》,洋洋120行将一部茶史入诗,写得气势非凡,令人喝彩。
文人爱故乡,亦极力推崇故乡茶。茶以诗名,茶以人传。文人与茶人合为一体,亦将茶文化一脉输入中国文化的血脉里。
茶的圣洁与清芬,成为文人馈赠之首选。以茶为礼、为寿,甚至兼馈煮茶之水,气醇风清传承至今。相传唐人刘禹锡以菊花粉和萝卜换白居易的六班茶;扬州八怪之一的茶仙汪士慎以《乞水图》换焦五斗的雪花水;清人厉鹗以一部《宋诗纪事》换大恒禅师的龙井茶留给文坛茶史连绵佳话。而文人收到茶礼,辄兴奋莫名,飞毫赋诗。
有明一代,散茶崛起,开创瀹饮之法,推动茶业繁盛,饮茶之风普及到社会各层面。大儒沈德符以敏锐嗅觉述评: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野获编补遗》)中国茶文化从兹在世界茶文化中以扛鼎之姿独树一帜。
于是嗜茶的文人不再清高,遇上真正茶人,必然顶礼膜拜。冒辟疆、钱谦益援笔记茶痴朱汝圭,董其昌、张岱着文赞茶家闵汶水茶文化的精神在向独立的人格拓展。
秋雨滂沱之时,冬雪霏霏之夜,我寻一把曼生壶,一只成化杯,泡一壶茶,自斟自啜,或听雨打芭蕉,或看雪舞群山。我把中国茶史上的文人茶人默默地数着,想着他们的故事。茶熟香温且自看,茶的滋味,就是养生、养气、养德的滋味啊!
一杯浅茶,一杯平民化的茶,一杯渗有禅味的茶,一杯去湿利肝明目的茶,一杯让你体味人生的茶;再借南宋罗大经的一句诗送给你: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
汉代文人与茶结缘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南北朝。但若论其缘起还要追溯到汉代。
茶成为文化,是从它被当作饮料,发现了它对人脑有益神、清思的特殊作用才开始的。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有的说自春秋,有的说自秦朝,有的说自汉代。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自汉代开始比较可考。根据有三:第一,有正式文献记载。这从汉人王褒所写《僮约》可以得到证明。这则文献记载了一个饮茶、买茶的故事。说西汉时蜀人王子渊去成都应试,在双江镇亡友之妻杨惠家中暂住。杨惠热情招待,命家僮便了去为子渊酤酒。便了对此十分不满,跑到亡故的主人坟上大哭,并说:“当初主人买我来,只让我看家,并未要我为他人男子酤酒。”杨氏与王子渊对此十分恼火,便商议以一万五千钱将便了卖给王子渊为奴,并写下契约。契约中规定了便了每天应做的工作,其中有两项是“武阳买茶”,“烹茶尽具”。就是说,每天不仅要到武阳市上去买茶叶,还要煮茶和洗刷器皿。这张《僮约》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西汉中期之事。我国茶原生地在云贵高原,后传人蜀,四川逐渐成为产茶盛地。这里既有适于茶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又富灌溉之利,汉代四川各种种植业本来就很发达,人工种茶从这里开始很有可能。《僮约》证明,当时在成都一带已有茶的买卖,如果不是大量人工种植,市场便不会形成经营交易。汉代考古证明,此时不仅巴蜀之地有饮茶之风,两湖之地的上层人物亦把饮茶当作时尚。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开始喜好饮茶的大多是文化人。王子渊就是一个应试的文人,写《凡将篇》讲茶药理的司马相如更是汉代的大文学家。在我国文学史上,楚辞、汉赋、唐诗都是光辉的时代。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扬雄,常并称“扬马”。恰巧,这两位大汉赋家都是我国早期的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扬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物,一个从文字语言角度:都谈到茶。有人说,著作中谈到茶,不一定饮茶。如果说汉代的北方人谈茶而不懂茶、未见茶、未饮茶尚有可能,这两位大文学家则不然。扬雄和司马相如皆为蜀人,王子渊在成都附近买茶喝,司马相如曾久住成都,焉不知好茶?况且,《凡将篇》讲的是茶作药用,其实,药用、饮用亦无大界限。可以说会喝茶者不一定懂其药理,而知茶之药理者无不会饮茶。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文人,常出入于宫廷。有材料表明汉代宫廷可能已用茶。宋人秦醇说他在一位姓李的书生家里发现一篇叫《赵后遗事》的小说,其中记载汉成帝妃赵飞燕的故事。说赵飞燕梦中见成帝,尊命献茶,左右的人说:赵飞燕平生事帝不谨,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飞燕梦中大哭,以致惊醒侍者。小说自然不能做信史,《赵后遗事》亦不知何人所作,但人们作小说也总要有些踪影。当时产茶不多,名茶更只能献帝王,这个故事亦可备考。司马相如以名臣事皇帝,怎知不会在宫中喝过茶?况且,他又是产茶胜地之人。相如还曾奉天子命出使西南夷,进一步深入到茶的老家,对西南物产及风土、民情皆了解很多。扬雄同样对茶的各种发音都清楚,足见不是人云亦云。所以,历代谈到我国最早的饮茶名家,均列汉之司马、扬雄。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云:“借问扬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故陆羽写《茶经》时亦说,历代饮茶之家,“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其实,从历史文献和汉代考古看,西汉时,贵族饮茶已成时尚,东汉可能更普遍些。东汉名士葛玄曾在宜兴“植茶之圃”,汉王亦曾“课僮艺茶”。所以,到三国之时,宫廷饮茶便更经常了。《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载:吴主孙皓昏庸,每与大臣宴,竟日不息,不管你会不会喝,都要灌你七大升。韦曜自幼好学,能文,但不善酒,孙皓暗地赐以茶水,用以代酒。
蜀相诸葛亮与茶有何关系史无明载,但吴国宫廷还饮茶,蜀为产茶之地,当更熟悉饮茶。所以,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诸葛亮与茶的传说。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当地百姓相传为孔明南征时所栽,被称为“孔明树。”据傣文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会人工栽培茶树,这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大体相当。可见,孔明也是个茶的知己。饮茶为文人所好,这对茶来说真是在人间找到了最好的知音。如司马相如、扬雄、韦曜、孔明之类,以文学家、学问家、政治家的气质来看待茶,喝起来自然别是一种滋味。这就为茶走向文化领域打下了基础。尽管此时茶文化尚未产生,但已露出了好苗头。
茶司马与茶马御史的历史渊源
茶马司是古代专门负责茶叶收购进贡皇宫及管理茶马互换交易的机构。
宋有都大提举茶马司,掌以川茶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换马匹。明初于洮州(治今甘肃临潭)、秦州(治今甘肃天水)、河州(治今甘肃临夏)等州,清于陕西、甘肃皆置茶马司,有大使、副便等官,其职掌与前代同。清初又曾于陕、甘二省置御史专管茶马司,通称茶马御史。
茶马司的历史渊源以茶易马,是我国历代统治阶段长期推行的一种政策。即在西南(四川、云南)产地和靠近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制订马法,茶马司以易马的职能,即边区少数民族用马匹换取他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
据史籍所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经略安抚使王韶在甘肃临洮一带与人木征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即令在四川征集,并在四川四路设立提兴茶马司,负责从事收购和以易马工作,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场和买马场,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茶马司)从事以易马交易,不准私贩,严禁商贩运到沿边地区去卖,甚至不准将籽、苗带到边境,凡贩私则予处死,或充军三千里以外,茶马司官员失察者也要治罪。立法如此严酷,目的在于通过内地来控制边区少数民族,强化他们的统治。这就是以治边的由来。但在客观上,茶马司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
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无此需要,而未实行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设立专门的茶马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西部增设北胜州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废止茶马司。
苏轼的咏茶诗词
苏东坡深研佛理,亦精通茶道,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咏茶诗词。东坡对饮茶一道,更深得独到之秘,对于茶叶、水质、器具、煎法,都颇讲究。
七绝一首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
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在杭州任通判时,一天,因病告假,游湖上净慈、南屏诸寺,晚上又到孤山谒惠勤禅师,一日之中,饮浓茶数碗,不觉病已痊愈。便在禅师粉壁上题了这首七绝诗。
试院煎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繞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今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娥眉,且学公家作茗饮。博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苏东坡烹茶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他认为好茶还须好水配,"活水还须活火烹"。他在《试院煎茶》诗中,对烹茶用水的温度作了形象的描述,他以沸水的气泡形态和声音来判断水的沸腾程度。
水调歌头已过几番风雨,前夜一声雷,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结就紫云堆。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此阙词记述了采茶、制茶、点茶的情景及品茶时的感觉,描述地极为生动传神。
次韵曹辅寄豁源试焙新芽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此诗虽称戏作,实乃倾注了东坡对茶茗的特殊情怀,特别是末句「从来佳茗似佳人」,以诙谐、浪漫的笔调着墨,更是历代文士茶人耳熟能详的名句。后来,人们将苏东坡的另一首诗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与"从来佳茗似佳人"辑成一联,陈列到茶馆之中,成为一副名联。
西江月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口汤发雪腴酽白,盞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词中提到以谷帘珍泉煎烹龙焙绝品,乃是人间茶品之极致。
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经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诗中前段描写月夜临江烹茶的情趣,后段则以茶茗与自然的翻覆变化,反衬世事的无常而平抚自己悲苦的境遇。
仇池笔记除烦去腻,不可缺茶,然暗中损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齿间,消缩脱去,不烦挑刺,而齿性便若缘此坚密。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数日一啜不为害也。此大有理。此词中介绍了一种以茶护齿的妙法。
和钱安道寄惠建茶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胸中似记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为君细说我未暇,试评其略差可听。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过始知真味永。纵复苦硬终可录,汲黯少戆宽饶猛。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忄广。体轻虽复强浮泛,性滞偏工呕酸冷。其间绝品岂不佳,张禹纵贤非骨鲠。葵花玉夸不易致,道路幽险隔云岭。谁知使者来自西,开缄磊落收百饼。嗅香嚼味本非别,透纸自觉光炯炯。比糠团凤友小龙,奴隶日注臣双井。收藏爱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幸。此诗有味君勿传,空使时人怒生瘿。诗中列举了各地名茶,而且他认为福建建溪茶为北宋全国之冠;双井茶为草茶第一。
次韵黄夷仲茶磨
前人初用茗饮时,煮之无问叶与骨。
浸穷厥味臼始用,复计其初碾方出。
计尽功极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创物。
破槽折杵向墙角,亦其遭遇有伸屈。
岁久讲求知处所,佳者出自衡山窟。
巴蜀石工强镌凿,理疏性软良可咄。
予家江陵远莫致,尘土何人为披拂。
这首诗主要介绍了茶臼、茶碾、茶磨等碾磨茶的器具,品茶人通常用这些工具将茶饼加工成末茶。
苏东坡一生,因任职或遭贬谪,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处,凡有名茶佳泉,他都留下诗词,他关于茶的诗词、文章还要许多,如他创作的散文《叶嘉传》,以拟人手法,形象地称颂了茶的历史、功效、品质和制作等各方面的特色。
又如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苏轼任徐州太守时作有《浣溪沙》一词:"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形象地再现了他思茶解渴的神情。
"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是描写杭州的"白云茶"。
"千金买断顾渚春,似与越人降日注"是称颂湖州的"顾渚紫笋"。
文人笔下的“茶典故”
有些茶的典故可能不全来自民间,而是出于文人之手或经过文人加工,但听起来仍是饶有趣味。如看人上茶的故事便很有意思。
相传清代大书画家、号称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镇江读书。一天他来到金山寺,到方丈室看别人字画,老方丈势力眼,见郑板桥衣着简朴,不屑一顾,仅勉强地招呼坐。又对小和尚说:茶!交谈中得知郑是同乡,于是又说:请坐!并喊小和尚:敬茶!而当老方丈得知来者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时,大喜,于是忙说:请上坐!又急忙吩咐小和尚:敬香茶!茶罢,郑板桥起身,老和尚请求赐书联墨宝,郑板桥乃挥手而书,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这副对联对得极妙,不仅文字对仗甚工,而且讽刺味道极浓。
还有一则朱元璋赐茶博士冠带的故事,说明太祖朱元璋一次晚宴后视察国子监,厨人献上一杯香茶,朱正在口渴,愈喝愈觉香甜,心血来潮,乘兴赐给这厨人一付冠带。院里有位贡生不服气,乃高吟道:十年寒窗下,不如一盏茶。众人看这贡生敢忤皇上,大惊,朱元璋却笑着对了个下联: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这个故事,一方面是说明朱元璋好茶,同时也较符合历史,朱氏出身低微,比较能体谅劳动者,自己又没读过多少书,重实务而轻书生,或许是真有的。
至于众说周知的敦煌变文茶酒论的故事,其本身很明显自民间故事脱胎而来。这个故事以赋的形式出现,说明已经过文人加工整理,有人考证其为五代到宋初的作品,那么在民间流传则应更早。而到明代又出现同样母题的茶酒争高的故事。同时,在藏族俗文学中也发现这个题材的作品。由此说明,民间故事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而在中国人心目中,向来把茶看得比酒要重一些。
唐代以前与武夷茶结缘的文人
闽越时期武夷山是否种茶,已不可考。但说到武夷茶,有一个人却不能不提,那就是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江淹是河南兰考人,字文通,出生于公元444年,卒于公元505年。历仕宋、齐、梁三代,可谓“三朝元老”。江淹幼年丧父,由母亲教他识字,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三岁识字,七岁能诗,很受当时文人推崇,大家尊称其为“江郎”。后来,江淹当上了官,文章写得少了,世人以为他才思已尽,于是有了“江郎才尽”这个成语。
且不论江郎是否才尽,单说江淹与武夷山结缘这件事,就足以说明他走上仕途后文采依然出众。江淹曾两次出任吴兴县令(浦城),在闽北留下大量足迹,至今在浦城、政和等地都有被命名为“笔架山”的山峰,这都是当地人为纪念江淹而起的。江淹在担任吴兴县令时曾游武夷,并在他的《江文通集》序言这样记到武夷山:“地处东南峤外,闽越之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芽,皆淹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也。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著文章自娱。”文中的“灵芽”指的就是茶,这应该是关于“武夷茶”最早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用“碧水丹山”来形容武夷山,江淹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据说,江淹离开武夷山后,曾梦见五彩的生花妙笔,写文章文思如泉涌,于是有了“梦笔生花”之说。
唐代的武夷山已颇具盛名。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派遣登仕郎颜行之诏封武夷山为“名川大山”,颁令禁止樵伐。据《福建简史》记载,茶是除了盐之外唐代福建唯一的特产,武夷山作为茶之精品自然也在其中。孙樵,字可之,关东人,唐代散文大家,生卒年均不详。他是一位监管国家勘界、绘制地图的职方员外郎,因工作需要来到武夷山,品饮武夷茶后深感珍奇,因此将之送给焦刑部,并赋诗一首《送茶与焦刑部书》(志书说送茶时间在元和年间,即公元806年到公元820年之间)。《送茶与焦刑部书》是这样写的:“甘晚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孙樵用甘晚侯比喻武夷茶,意指滋味厚重、先苦后甘,回甘晚,但非常持久。后来,清代的蒋蘅写了《晚甘侯传》一文,其实与孙樵的甘晚侯是一个意思,只是用词方法不同而已,均符合岩茶提倡的岩骨花香之意。从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可以了解到,武夷茶从一出现就成为了人们馈赠亲友的佳品。
唐代与武夷茶结缘的还有晚唐诗人徐夤。徐夤是唐朝进士,唐朝灭亡后,他参加了五代十国中闽国的科举,高中状元,被闽王王审知任命为国相,主持国事。根据史料,徐夤的生卒年不详,仅知道他字昭梦,莆田籍贯。他的《尚书惠蜡面茶》是武夷山最早的茶诗,至今已有1100多年。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记叙了唐时期武夷茶作为蒸汽绿茶的采摘时间、制作工艺,它对后人考证唐代茶史起了重要作用。
从江淹、孙樵、徐夤各自所处的年代看来,唐以前的三、四百年间,中国茶市正从西南逐渐向东南推移,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在武夷山试种、试做武夷岩茶的事迹,说明了武夷茶由于其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而品质优异,从一开始就脍炙人口,作为中国品牌最持久的名茶而闻名于世。
文人与禅家,生活与修行——中日茶风的分野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国人谈日本文化,向喜从它诸事皆以中国为师说起,而在保留中国唐宋古风上,日本之于中国亦多有礼失而求诸野之处,以是,对日人民族性于外来文化之迎拒乃至接受后之本土化历程乃常忽略。由此谈中日文化之比较与借鉴,自不免偏颇。
日本对中国文化之迎拒,古琴是明显例子。唐时虽胡乐兴盛,琴仍长足发展,宋时更因汉本土文化复兴而管领风骚,明季琴书大量印行,琴派繁衍,而此三时代,日本接受中国大量影响,却独不见严格意义下唯一的文人乐器古琴在日本扎根,仅明末清初永福寺东皋心越所传东皋琴派以寥寥之姿寂寞传承,可见日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原自有它文化主体的选择在。
这主体选择,迎拒外,更需注意的,是因应自身需要的本土化作为,以此,日本许多事物虽都自外引入,却又深具日本特质,而茶道则为其中之大者。
茶禅一味是茶文化中人人朗朗上口的标举,但它其实并不见于卷帙浩繁的中国禅籍,而系出自《碧岩录》作者圜悟克勤东流日本的墨宝拈提,但就这一墨宝拈提,却开启并引导了日本近千年的茶道轨迹。
直言之,日本茶道由禅而启,自来就是禅文化的一环。而禅,宋时以临济、曹洞分领天下,宗风大别。临济禅生杀临时,开阖出入,宗风峻烈;曹洞禅默观独照,直体本然,机关不露。以此不同之风光,临济影响了武士道,而茶道、花道、俳句、枯山水等,则依于曹洞。更直接地讲,日人民族性中之菊花与剑,一收一放,看似两极,西方甚至以之为矛盾之民族性格,其实皆立于禅。剑,乃生杀之事,与临济多相关;菊花,固诗人情性,则以曹洞为家风。
曹洞默照,日本禅艺术多透露着这层消息:花道当下静处,俳句直下会心,而枯山水更不似可以观、可以游、可以赏、可以居的中国园林,它只让行者独坐其前,直契绝待。茶道则在小小的茶寮中透过单纯极致的行茶,让茶人茶客直入空间、茶味、器物,乃至煮水声,以契于一如。
除了曹洞默照的影响,日本茶道之形成规矩严整的形式,也缘于日人向以秩序闻名之民族性。此民族性既因于地小人稠,天灾又多,需更强之群体性才好生存的环境,也缘于单一民族的单纯结构,及万世一系的天皇与封建制度。总之,日本之为一秩序性民族固不待言。也因此,以外规形塑内在,乃成为日人贯穿于生活、艺术、修行的明显特征。而茶道,即经由不逾之规矩,日复一日之磨炼,将心入于禅之三昧。
默照禅的机关不露,澄然直观,正能在最简约的条件下与物冥合,故茶寮简约,茶室数叠,器物亦皆内敛。在此,要的不是放,是收;不是繁华,是简约;不是率性,是规范。茶味本身更不是目的,一切都为了达致禅之三昧。
日本茶道如此,中国茶艺不然,许多地方甚且相反。
中国茶艺历史悠久,却几度变迁,叶茶壶泡之形式起自于明,论历史,并不早于抹茶道。日本茶道依禅而立,中国茶艺则立基文人,尽管宋后文人常有与禅亲近者,但根柢情性毕竟有别。
文人系世间通人,他原有钟鼎及山林两面,所谓达则仕,不达则隐,此仕是儒,此隐则为道。中国文人多外儒内道。外儒是读书致仕,经世致用;内道,则多不以老庄哲思直接作为生命之指引,更毋论齐万物、一得失之终极解脱,它主要以艺术样态而现,为文人在现实之外开启生命的另一空间,使其在现世困顿中得一寄情之安歇。
这艺术,以自然为宗,映现为基点,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向往,作用于具体,则有田园诗、山水画、园林、盆栽等艺术形式之设,而茶则为其中一端。
茶产于自然,成于人文,固成就不同之茶性,饮之,却都可回溯山川。而尽管茶艺中,亦有标举儒家规范者,近世尤其在台湾,也多有想从中喝出禅味者,但大体而言,道家美学仍是中国茶艺之基点,以茶席契于自然仍是重要的切入,而此切入则又以生活艺术的样貌体现着。
正如中国之园林与文人之山水,中国茶之于生命,更多的是在生活中的寄情,让日常中另有一番天地,它是典型的生活艺术,人以此悠游,不像禅般,直讲翻转生命。
正因寄情、悠游,中国茶艺乃不似日本茶道般万缘皆放,独取一味。直抒情性的茶艺,总不拘一格。文人既感时兴怀,触目成文,茶席多的就是自身美感与怀抱的抒发。而文人现实济世之道固常多舛,此抒发乃更多地在放怀,于是啜茶味、品茶香、识茶器、观茶姿乃至以诗、以乐相互酬唱,就成茶席雅事。在此,多的是人世的挥洒、生活的品味,较少修行的锻炼、入道的观照。
此外,中国茶在唐宋虽有一番风貌,典型地成为文人艺术则在明代,明季政治黑暗,文人外不能议论时政,就只能在唯美世界中排遣自己,明代茶书因此尽多对茶物茶事之讲究,却少茶思之拈提。这也使茶艺极尽生活之所能,物不厌其精,行不嫌其美。其高者,固能映现才情;其末者,也就流为逐物迷心之辈。
谈中日茶文化,这文人与禅家、生活与修行确是彼此根本的分野所在,它缘于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最终形成自哲思、美学以迄器物、行茶皆截然有别的两套系统。而也因这根柢分野,率意地在彼此间作模拟臧否乃常有见树不见林之弊。在此,无可讳言地,总以茶文化宗主国自居的中国,其识见尤多以己非人之病。
然而,虽说不能率意臧否,但特质既成对比,正好可资映照,以人观己,乃多有能济己身之不足者。
就此,日本茶道虽言一门深入而契于三昧,虽言以外境型塑内心,但长期以降,日人在茶道上的观照,也常因泥于规矩而老死句下。到日本参与茶席,所见多的是只得其形、未得其旨之辈,如千利休等人之标举,竟常只能在文献中寻。
得其形,未得其旨,日人的茶道修行,在今日正颇有中国默照禅开山祖天童宏智所言,住山迹陈之病,而此迹陈,正需行脚句亲来治。此行脚,在佗寂的基点上,或可尝试注入临济乃至中国不同之禅风,使其另有风光。另外,则在多少让其能不泥于狭义之修行样态。
修行,不只住山,不只行脚;修行,还可在生活。千利休晚年说茶道,是烧好水,泡好茶,是冬暖之,夏凉之而已,其实正预示了大道必易,毕竟,能在日常功用中见道,才真好凡圣一如。
此凡圣一如,在日本,须体得由圣回凡,在中国,却相反地,须观照由凡而圣。文人挥洒情性,虽看似自在无碍,却多的是自我的扩充,乃至物欲的张扬,即便不然,也常溺于美感、耽于逸乐,因此更须回归返照,由多而一,由外而内,由情性的流露到道艺的一体,而日人之茶道恰可在此为参照。直言之,要使中国茶艺不溺于自我,禅,就是一个必要的观照。
禅,原在中国大成而东传日本,宋后,汉本土文化重兴,宋明之儒者多受禅影响却又大力辟禅,而即便有近禅者,亦多狂禅文字禅之辈,是以禅附和文人。日本禅则不然,无论临济之开阖、曹洞之独照,其禅风皆孤朗鲜明,恰可济文人之病。
谈禅家与文人、修行与生活,此文化之差异,当然不只在茶。就画,宋后文人画居主流,禅画却东流日本且开后世济济风光,这画风之分野亦可参照。而就此,坦白说,谈中日文化尤其是茶,虽历史中有宗主输入之分,有千丝万缕之缘,但与其入主出奴,倒不如将两者视为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反可从其中识得彼此之殊胜与不足,而在不失自身基点上更成其大,更观其远。
国人谈日本文化,向喜从它诸事皆以中国为师说起,而在保留中国唐宋古风上,日本之于中国亦多有礼失而求诸野之处,以是,对日人民族性于外来文化之迎拒乃至接受后之本土化历程乃常忽略。由此谈中日文化之比较与借鉴,自不免偏颇。
日本对中国文化之迎拒,古琴是明显例子。唐时虽胡乐兴盛,琴仍长足发展,宋时更因汉本土文化复兴而管领风骚,明季琴书大量印行,琴派繁衍,而此三时代,日本接受中国大量影响,却独不见严格意义下唯一的文人乐器古琴在日本扎根,仅明末清初永福寺东皋心越所传东皋琴派以寥寥之姿寂寞传承,可见日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原自有它文化主体的选择在。
18世纪晚期日本江户时代的绘画作品描绘了一家人新年团聚时喝茶聚餐的情景
这主体选择,迎拒外,更需注意的,是因应自身需要的本土化作为,以此,日本许多事物虽都自外引入,却又深具日本特质,而茶道则为其中之大者。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茶禅一味是茶文化中人人朗朗上口的标举,但它其实并不见于卷帙浩繁的中国禅籍,而系出自《碧岩录》作者圜悟克勤东流日本的墨宝拈提,但就这一墨宝拈提,却开启并引导了日本近千年的茶道轨迹。
直言之,日本茶道由禅而启,自来就是禅文化的一环。而禅,宋时以临济、曹洞分领天下,宗风大别。临济禅生杀临时,开阖出入,宗风峻烈;曹洞禅默观独照,直体本然,机关不露。以此不同之风光,临济影响了武士道,而茶道、花道、俳句、枯山水等,则依于曹洞。更直接地讲,日人民族性中之菊花与剑,一收一放,看似两极,西方甚至以之为矛盾之民族性格,其实皆立于禅。剑,乃生杀之事,与临济多相关;菊花,固诗人情性,则以曹洞为家风。
曹洞默照,日本禅艺术多透露着这层消息:花道当下静处,俳句直下会心,而枯山水更不似可以观、可以游、可以赏、可以居的中国园林,它只让行者独坐其前,直契绝待。茶道则在小小的茶寮中透过单纯极致的行茶,让茶人茶客直入空间、茶味、器物,乃至煮水声,以契于一如。
除了曹洞默照的影响,日本茶道之形成规矩严整的形式,也缘于日人向以秩序闻名之民族性。此民族性既因于地小人稠,天灾又多,需更强之群体性才好生存的环境,也缘于单一民族的单纯结构,及万世一系的天皇与封建制度。总之,日本之为一秩序性民族固不待言。也因此,以外规形塑内在,乃成为日人贯穿于生活、艺术、修行的明显特征。而茶道,即经由不逾之规矩,日复一日之磨炼,将心入于禅之三昧。
默照禅的机关不露,澄然直观,正能在最简约的条件下与物冥合,故茶寮简约,茶室数叠,器物亦皆内敛。在此,要的不是放,是收;不是繁华,是简约;不是率性,是规范。茶味本身更不是目的,一切都为了达致禅之三昧。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日本茶道如此,中国茶艺不然,许多地方甚且相反。
中国茶艺历史悠久,却几度变迁,叶茶壶泡之形式起自于明,论历史,并不早于抹茶道。日本茶道依禅而立,中国茶艺则立基文人,尽管宋后文人常有与禅亲近者,但根柢情性毕竟有别。
文人系世间通人,他原有钟鼎及山林两面,所谓达则仕,不达则隐,此仕是儒,此隐则为道。中国文人多外儒内道。外儒是读书致仕,经世致用;内道,则多不以老庄哲思直接作为生命之指引,更毋论齐万物、一得失之终极解脱,它主要以艺术样态而现,为文人在现实之外开启生命的另一空间,使其在现世困顿中得一寄情之安歇。
这艺术,以自然为宗,映现为基点,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向往,作用于具体,则有田园诗、山水画、园林、盆栽等艺术形式之设,而茶则为其中一端。
茶产于自然,成于人文,固成就不同之茶性,饮之,却都可回溯山川。而尽管茶艺中,亦有标举儒家规范者,近世尤其在台湾,也多有想从中喝出禅味者,但大体而言,道家美学仍是中国茶艺之基点,以茶席契于自然仍是重要的切入,而此切入则又以生活艺术的样貌体现着。
正如中国之园林与文人之山水,中国茶之于生命,更多的是在生活中的寄情,让日常中另有一番天地,它是典型的生活艺术,人以此悠游,不像禅般,直讲翻转生命。
正因寄情、悠游,中国茶艺乃不似日本茶道般万缘皆放,独取一味。直抒情性的茶艺,总不拘一格。文人既感时兴怀,触目成文,茶席多的就是自身美感与怀抱的抒发。而文人现实济世之道固常多舛,此抒发乃更多地在放怀,于是啜茶味、品茶香、识茶器、观茶姿乃至以诗、以乐相互酬唱,就成茶席雅事。在此,多的是人世的挥洒、生活的品味,较少修行的锻炼、入道的观照。
此外,中国茶在唐宋虽有一番风貌,典型地成为文人艺术则在明代,明季政治黑暗,文人外不能议论时政,就只能在唯美世界中排遣自己,明代茶书因此尽多对茶物茶事之讲究,却少茶思之拈提。这也使茶艺极尽生活之所能,物不厌其精,行不嫌其美。其高者,固能映现才情;其末者,也就流为逐物迷心之辈。
谈中日茶文化,这文人与禅家、生活与修行确是彼此根本的分野所在,它缘于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最终形成自哲思、美学以迄器物、行茶皆截然有别的两套系统。而也因这根柢分野,率意地在彼此间作模拟臧否乃常有见树不见林之弊。在此,无可讳言地,总以茶文化宗主国自居的中国,其识见尤多以己非人之病。
然而,虽说不能率意臧否,但特质既成对比,正好可资映照,以人观己,乃多有能济己身之不足者。
就此,日本茶道虽言一门深入而契于三昧,虽言以外境型塑内心,但长期以降,日人在茶道上的观照,也常因泥于规矩而老死句下。到日本参与茶席,所见多的是只得其形、未得其旨之辈,如千利休等人之标举,竟常只能在文献中寻。
得其形,未得其旨,日人的茶道修行,在今日正颇有中国默照禅开山祖天童宏智所言,住山迹陈之病,而此迹陈,正需行脚句亲来治。此行脚,在佗寂的基点上,或可尝试注入临济乃至中国不同之禅风,使其另有风光。另外,则在多少让其能不泥于狭义之修行样态。
修行,不只住山,不只行脚;修行,还可在生活。千利休晚年说茶道,是烧好水,泡好茶,是冬暖之,夏凉之而已,其实正预示了大道必易,毕竟,能在日常功用中见道,才真好凡圣一如。
此凡圣一如,在日本,须体得由圣回凡,在中国,却相反地,须观照由凡而圣。文人挥洒情性,虽看似自在无碍,却多的是自我的扩充,乃至物欲的张扬,即便不然,也常溺于美感、耽于逸乐,因此更须回归返照,由多而一,由外而内,由情性的流露到道艺的一体,而日人之茶道恰可在此为参照。直言之,要使中国茶艺不溺于自我,禅,就是一个必要的观照。
禅,原在中国大成而东传日本,宋后,汉本土文化重兴,宋明之儒者多受禅影响却又大力辟禅,而即便有近禅者,亦多狂禅文字禅之辈,是以禅附和文人。日本禅则不然,无论临济之开阖、曹洞之独照,其禅风皆孤朗鲜明,恰可济文人之病。
谈禅家与文人、修行与生活,此文化之差异,当然不只在茶。就画,宋后文人画居主流,禅画却东流日本且开后世济济风光,这画风之分野亦可参照。而就此,坦白说,谈中日文化尤其是茶,虽历史中有宗主输入之分,有千丝万缕之缘,但与其入主出奴,倒不如将两者视为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反可从其中识得彼此之殊胜与不足,而在不失自身基点上更成其大,更观其远。
茶趣| 茶史漫谈:茶与魏晋风度
公元三四世纪,随着巴蜀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饮茶的风俗沿长江中下游流传开来。魏晋南北朝时,在江南,包括东南沿海,饮茶之风在世族士族中日盛,成为社会活动的一种媒介。
在这种风气感染下,永嘉之乱后,从北方南渡的豪门士族也有不少喜好饮茶。
史载,三国东吴的韦昭,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县)人。少好学,善文章,著有《孝经注》、《论语注》、《国语注》等书。东吴末帝孙皓在位时,封高陵亭侯,迁中坊仆射,后为侍中,尝邻左国史。
也许长期生活在江南,他喜饮茶,却不善喝酒。偏偏遇上孙皓在位16年,常宴饮群臣,不醉无归。而且,还找来黄门郎10人,作为宴会监酒司过;宴罢,令各奏其过,以朝谑公卿,举发私短为欢。
酒量不过三升的韦昭,参加宴饮时,偷偷以茶代酒。结果,孙皓以不奉诏命,于凤凰二年(273年)收韦昭入狱。
不奉诏命罪,貌似因以茶代酒起;其实,祸起于当年孙皓即位,欲为其父孙和入史书作纪,而修史的韦昭却以孙和不登帝位,只有资格作传,由此触怒孙皓。积前后嫌怨,韦昭在狱中也就难逃一死。
以士风而论,韦昭一介儒学之士,并非主张任情废礼的玄学,冲击传统旧礼法;然而,只要抗君命,逆龙鳞,一桩小小的茶饮事件,也会弄掉了脑袋。
汉末到晋末,士族阶层开始形成、发展。当时,战乱频频,社会动荡,士风活跃,传统的旧礼法不足以适应已变化的社会状态。
但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固然分明;就是士族与世族之间,世族与世族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甚至不是门当户对,不通婚姻。《世说新语》录有二则有趣的茶饮故事:
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太傅禇衺(字季野)初过江后,来到苏州,正巧当地的豪强大族在金阊亭(今苏州阊门)会聚饮茶。
虽然禇太傅官高名重,但乍到江南,却不为人识。于是,被人吩咐左右特别关照:多斟茶水,不断添续,尽量少给佐茶的蜜渍瓜果,让禇衺始终吃不上。明知受到轻侮,禇太傅倒也沉得住气。
直至饮罢,他才徐徐举手,对众人报上姓名:禇季野。一下子,四座大惊而散,无不狼狈。难怪人称禇季野皮里阳秋,意即外表虽不言语,而四时之气蕴备。说来令人可笑,那时连饮茶也非得分个三五九等。
另一则故事与号称仲父的王导(字茂弘)有关。王导出身士族,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任丞相。当他悉知任瞻过江南渡,便邀上先渡江的名人贤士一起,列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迎接。
说起任瞻,字育长,乐安人,与王导属山东老乡,官宦子弟。年少时,颇有美名,形象俊朗,神明可爱。当时的权贵王戎选女婿,任瞻被列入四名候选之一。可是,他自过一江,人便变糊涂了。
王导与任瞻一见面,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众人入席坐下,茶水一送上来,任瞻便问:此为茶为茗?茗,即晚采的茶叶。旁人一听,面露怪异的神色。
任瞻觉察后,又自我解释:刚才问是热的,还是冷的?尽管如此,王导还是按照昔日在北方时一样,热情相待。
这种待人之道,容人之量,可见王导历仕元、明、成三帝,廿多年间,能够领导南迁士族,联合江南士族,稳定东晋在南方的统治,自有过人之处。
茶饮,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既平常又普通,却可窥魏晋风度一二。(来源:羊城晚报李树政)